目录
快速导航-
叙事 | 能饮一杯无
叙事 | 能饮一杯无
-
叙事 | 鲸落
叙事 | 鲸落
-
叙事 | 西亚的背影
叙事 | 西亚的背影
-
叙事 | 五行
叙事 | 五行
-
叙事 | 迟到二十三年的葬礼
叙事 | 迟到二十三年的葬礼
-
叙事 | 男人与树
叙事 | 男人与树
-
叙事 | 德彪
叙事 | 德彪
-
叙事 | 鱼跃冲顶
叙事 | 鱼跃冲顶
-
叙事 | 协议生育
叙事 | 协议生育
-
叙事 | 拍打尘埃
叙事 | 拍打尘埃
-
散笔 | 巨石只是我们的名字
散笔 | 巨石只是我们的名字
-
散笔 | 当我步入老龄
散笔 | 当我步入老龄
-
散笔 | 群鸟低翔
散笔 | 群鸟低翔
-
新乡土 | 迷宫游戏
新乡土 | 迷宫游戏
-
新乡土 | 花椒树下的土丘
新乡土 | 花椒树下的土丘
-
吟咏 | 出离宫记
吟咏 | 出离宫记
-
吟咏 | 八月的石榴
吟咏 | 八月的石榴
-
吟咏 | 荒野叙事
吟咏 | 荒野叙事
-
吟咏 | 所有的路都通向我们的未来
吟咏 | 所有的路都通向我们的未来
-
吟咏 | 最后的平原
吟咏 | 最后的平原
-
吟咏 | 叩问桃木
吟咏 | 叩问桃木
-
知见 | 故乡的地方性与普遍性辨析
知见 | 故乡的地方性与普遍性辨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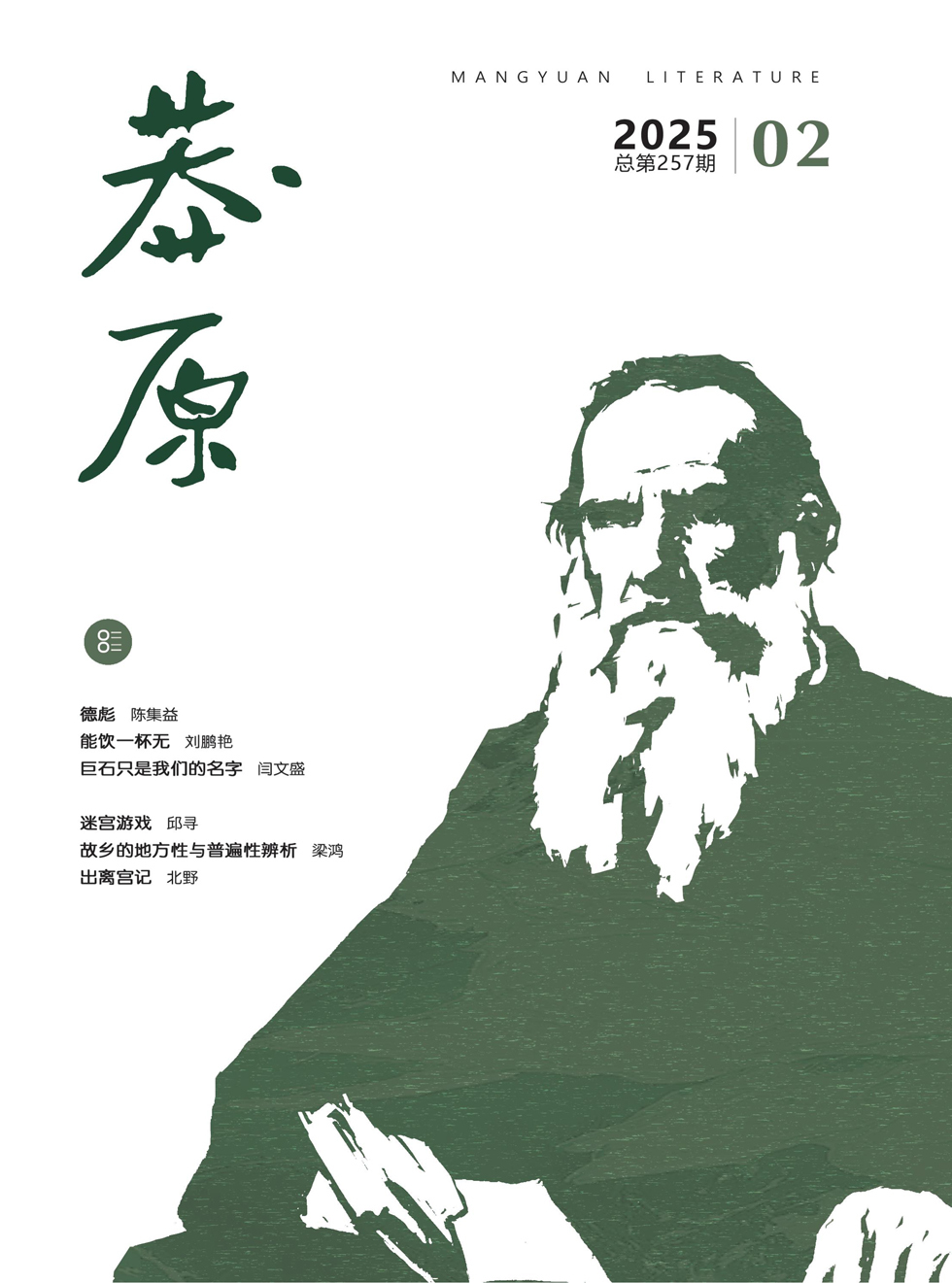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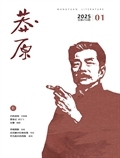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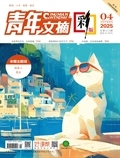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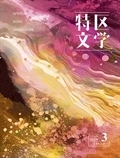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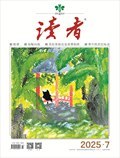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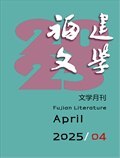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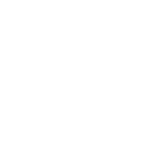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