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卷首语 | 战胜生活
卷首语 | 战胜生活
-

独家关注 | 巴金一百二十周年诞辰
独家关注 | 巴金一百二十周年诞辰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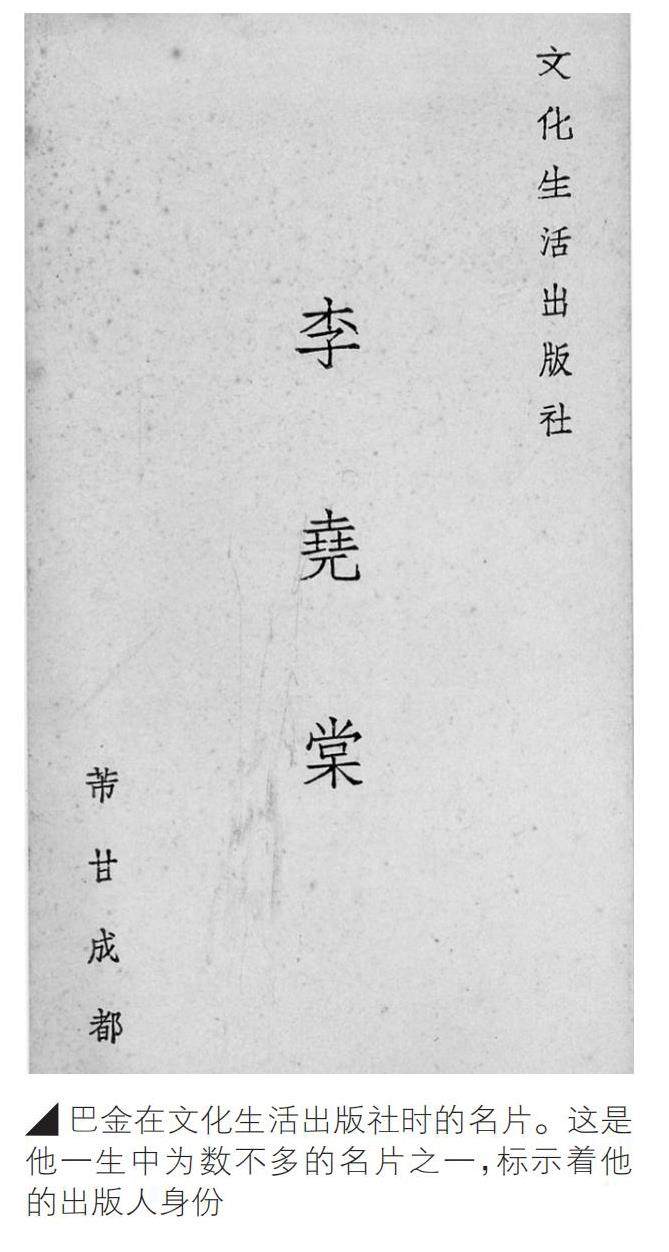
独家关注 | 拿几本新书献给读者,是莫大的快乐
独家关注 | 拿几本新书献给读者,是莫大的快乐
-

独家关注 | 巴金与“黎明”的难忘往事
独家关注 | 巴金与“黎明”的难忘往事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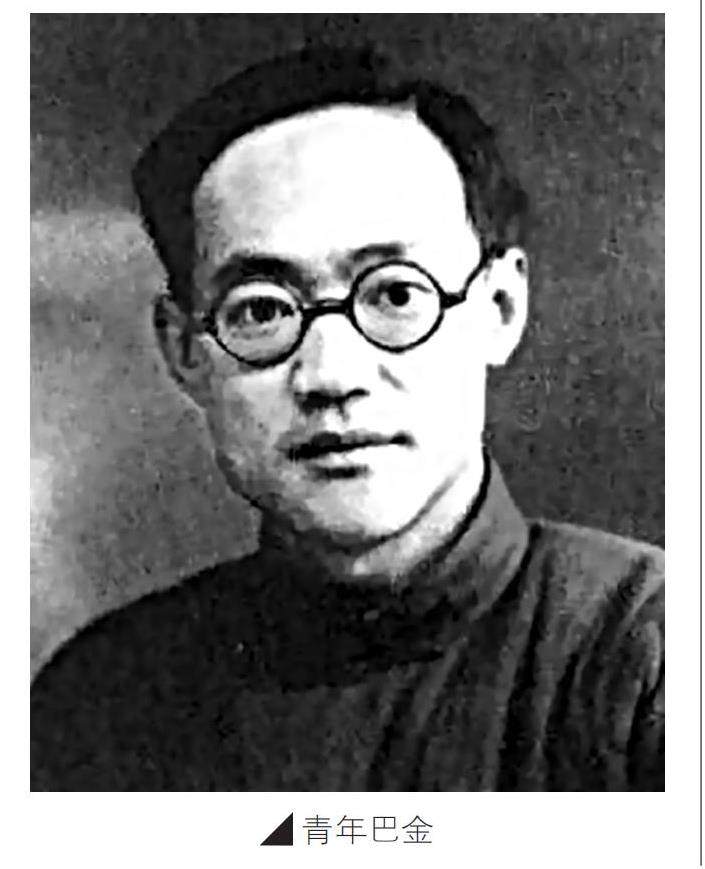
独家关注 | 晚年巴金的清醒之痛
独家关注 | 晚年巴金的清醒之痛
-

往事故人 | 新中国体育奠基者——贺龙
往事故人 | 新中国体育奠基者——贺龙
-

往事故人 | 吴镜汀、吴光宇:家国风雨昆仲情
往事故人 | 吴镜汀、吴光宇:家国风雨昆仲情
-

往事故人 | 诺贝尔兄弟何以成为“巴库石油大王”
往事故人 | 诺贝尔兄弟何以成为“巴库石油大王”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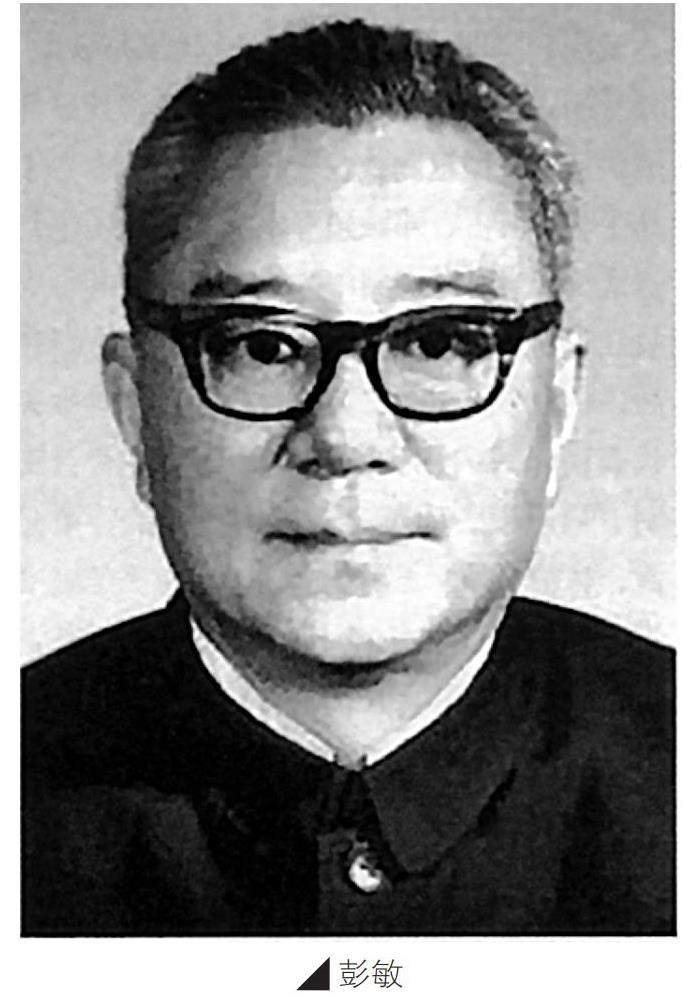
往事故人 | 彭敏:勇当开路先锋的“红色专家”
往事故人 | 彭敏:勇当开路先锋的“红色专家”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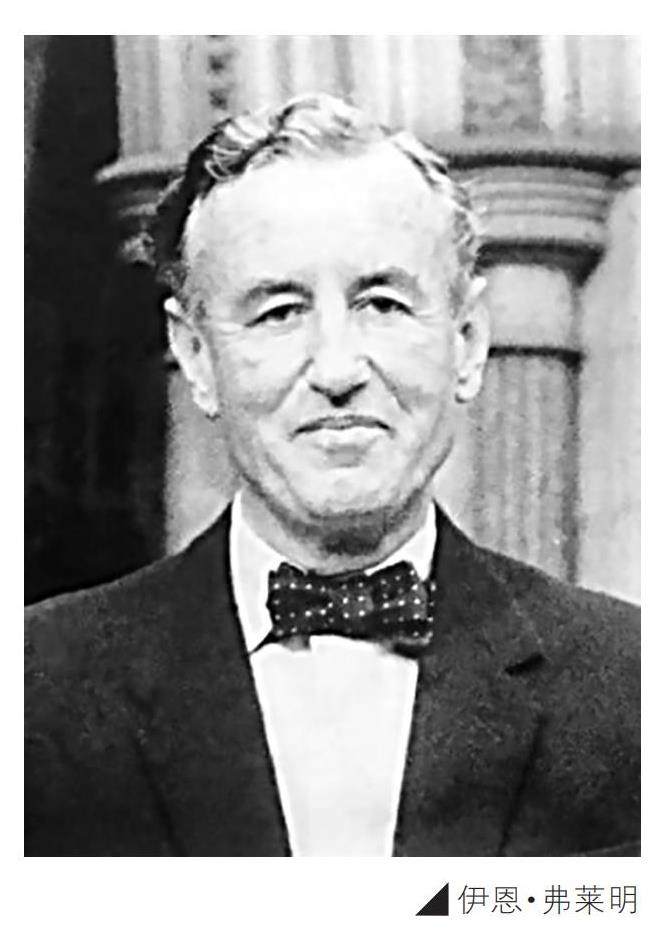
往事故人 | “007之父”伊恩·弗莱明的传奇人生
往事故人 | “007之父”伊恩·弗莱明的传奇人生
-

往事故人 | 梅兰芳的苏州之行
往事故人 | 梅兰芳的苏州之行
-

往事故人 | 萧红处女作首次刊发始末
往事故人 | 萧红处女作首次刊发始末
-

今日名流 | “最美医生”路生梅:为佳县人民服务终生
今日名流 | “最美医生”路生梅:为佳县人民服务终生
-

今日名流 | 翟墨:与海共舞(下)
今日名流 | 翟墨:与海共舞(下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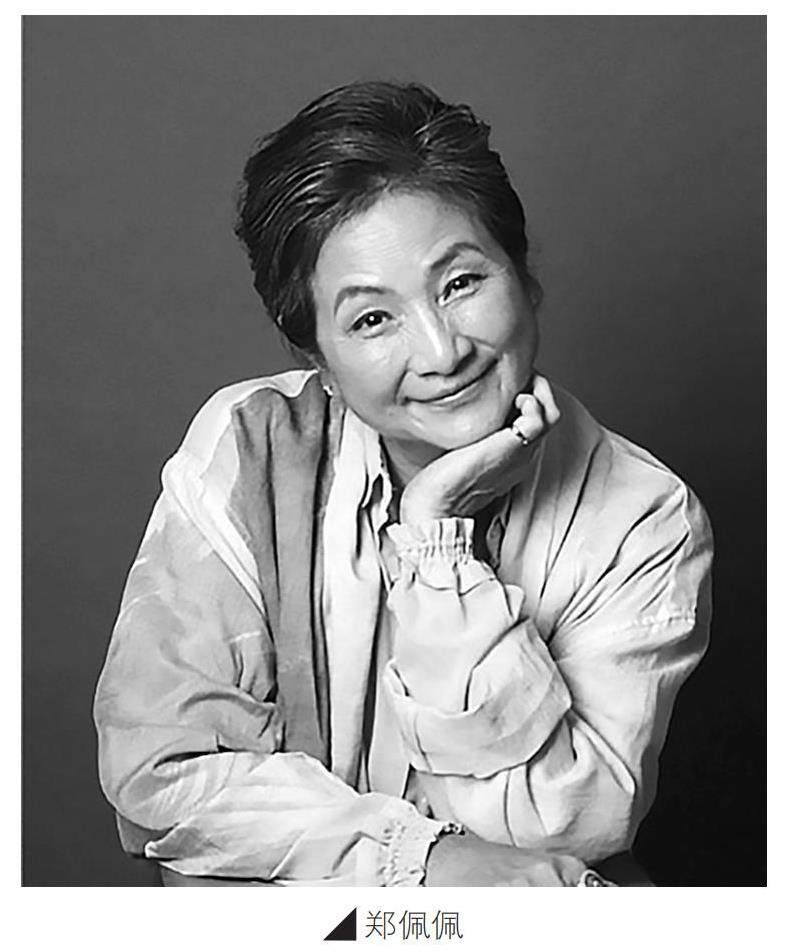
今日名流 | 郑佩佩:回首一笑七十年
今日名流 | 郑佩佩:回首一笑七十年
-

专栏 | 卜键的书房:时空转换,不变的是阅读和写作
专栏 | 卜键的书房:时空转换,不变的是阅读和写作
-

专栏 | 微名人
专栏 | 微名人
-

专栏 | 第一代中国女排姑娘高霭鸿
专栏 | 第一代中国女排姑娘高霭鸿
-

专栏 | 影片《大地》与诺贝尔文学奖
专栏 | 影片《大地》与诺贝尔文学奖
-
专栏 | 《中国莎士比亚学研究的引路人——孙家琇》读后感
专栏 | 《中国莎士比亚学研究的引路人——孙家琇》读后感
-
专栏 | 追寻莎士比亚学专家孙家琇
专栏 | 追寻莎士比亚学专家孙家琇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